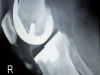虛心學習:東方演員與西方劇場的偶遇
二○一○年我在劇場界有一場奇遇,這是我過去連做夢都想不到的事,卻真實發生了。還記得某天突然接到國家戲劇院的聯繫,告訴我二○一○年兩廳院台灣國際藝術節將邀請國際大導演羅伯.威爾森(Robert Wilson)跨國合作一齣名為《鄭和1433》的戲,導演想找位台灣戲曲演員合作,院方列出名單,詢問我是否有意願參與,這麼難得的機緣,我當然一口答應。
(圖片來源:圓神出版社)
羅伯.威爾森導演第一次來台開會的時候,正巧遇上唐美雲歌仔戲團在劇院演出《宿怨浮生》,原定安排到現場看演出卻不幸感冒,劇院人員猜測他可能看了半場就會離開休息,沒想到導演竟看完全場,然後告訴工作人員:「不用再找別人了,就是她,今天因為身體不適,改天再約Ms. 唐碰面。」導演離開後,工作人員到後台轉述他的話,我當然很驚喜,對未來的工作充滿期待。
信任導演,完全交託
羅伯.威爾森是誰?他於二○○九年執導的《歐蘭朵》在兩廳院首演引起轟動,《鄭和1433》是他第二度來台灣執導的戲。羅伯.威爾森導演以前衛的劇場風格聞名,也是位舞台設計名家,他用極簡的視覺、精準的燈光設計,將光線與空間規畫營造出獨特的風格。
合作過程中,我也親身體驗到羅伯.威爾森導演對燈光的要求。他曾為了一個舞台上的小燈泡而堅持等待一個下午,我本來內心還有一點質疑,舞台上有數百個燈泡,少一個會有影響嗎?但後來我還真是佩服,他的堅持讓我見識到一個小拇指般大小的燈泡也是舞台上不能或缺的要角,也能左右觀眾的視覺感受。
那年我的工作其實已忙到焦頭爛額,劇團除了與廈門歌仔戲團談合作《蝴蝶之戀》外,同時也正忙於《宿怨浮生》的公演,我自己還要拍電視劇《娘家》,沒日沒夜的跑場一直是我生活的日常寫照。很多朋友問我,已經忙得這樣日夜不分,為何還要接這個跨國合作的戲?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很想了解西方劇場的工作模式,希望藉此機會近距離觀察導演的手法和技巧,雖然扮演的說書人只是個小角色,但抱著學習的角度參與就能有不同的收穫。
坦白說,一開始會答應也是因為這個角色是只有三場戲的串場人物,衡量之下應該不至於影響日常工作,但有時真的只能嘆「人算不如天算」,日後的變化讓我有些措手不及,但既然決定接了,也就開心接受所有挑戰。
《鄭和1433》是以著名航海家鄭和的第七次航行切入,描寫壯舉背後的辛酸血淚,以及夢想的追尋與失落。羅伯.威爾森導演要將不同文化的人與音樂交融在一起,共同編織這場音樂劇場美學。對我來說也是個很好的機緣,藉由導演的手法讓觀眾看見歌仔戲演員另一種表演風貌。我除了要用歌仔戲小生的唱腔演唱古典詩詞,還要以美國知名爵士樂大師歐涅.柯曼(Ornette Coleman)與迪奇.蘭德利(Dickie Landry)的音樂來詮釋,這場歌仔戲與爵士樂的結合讓我更深刻體會音樂與音效對一齣戲劇的重要性。
羅伯.威爾森導演曾說過,《鄭和1433》描述的是十五世紀,一個東方人前往西方的旅程。對比現今,是身為西方人的他在東方(台灣)創作,這個有趣的巧合讓這齣戲有了探索歷史的另一種角度。導演強烈的個人風格也像汪洋中掌舵的船長,帶領演員與觀眾一同探索這趟自由的航行。
羅伯.威爾森導演在台灣排完第一次戲就回美國了,當他再度來台時,大家已經在舞台排練了,沒想到導演竟然把之前的排練完全推翻,重頭來過,而我則由原來的說書人串場增加成一人分飾六、七個角色。資深副導告訴我,他跟著導演跑遍世界各國,導演的工作模式就是這樣,一開始不會給出特定演出模式,等看到演員的演出再做調整,遇到資質優秀的演員就會不斷加戲。副導說:「Ms. 唐,妳應該高興啊!」原來如此,既然導演如此信任我,那我當然更該全力以赴。
沒想到隨著演出時間愈來愈近,導演還是不斷修戲、加戲,甚至到演出前一天還在修戲,我也拿出歌仔戲演員的專業精神,竭盡全力跟隨導演拚戲。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導演說什麼妳都說好?」我說:「因為他是導演,我是演員,他願意給我建議甚至幫我加戲,正是因為肯定我、信任我,我當然應該心懷感謝。」而且我認定,導演是個塑造者、角色開創者,演員必須完全交託,依導演的要求去做,才能讓整齣戲的調性更為完整。
努力接球,挑戰能力與極限
這次經驗對我來說是演藝生涯的大考驗,尤其和那位德州來的,百老匯知名爵士音樂老師歐涅.柯曼的互動,最讓我驚奇。他擅長大膽且毫無拘束的即興演奏,可以說將自由爵士發展到了極致,常讓我聽得目瞪口呆。每次表演也是完全即興,兩人互丟想法也都必須立即吸收轉化,所以每次上場大家都會為我捏把冷汗,但我並不害怕,反而充滿新鮮感,期待他今天會出什麼招。
(圖片來源:圓神出版社)
導演也常出難題給我,記得有一天,導演問:「Ms. 唐,妳知不知道美國很多大城市的街頭都有拾荒老人?」我說:「我只在影集中看過。」於是導演要我想像自己是個拾荒老人並發出笑聲,我硬著頭皮試了七、八種不同笑聲給他,現在說來或許好笑,但當時我真的非常認真嚴謹的揣摩,導演也閉上眼睛專心聆聽我的笑聲,然後告訴我他要第幾個。走位也同樣一絲不苟,有一幕要求老人自言自語走到定點猛回頭,然後一個燈光打在臉上,就為這麼一個點,我們重來了無數次,務求百分之百精準。
我們在舞台上的排練都是很早就著裝演出,包括劇服和妝容都是完整的。根據副導的說法,這是因為舞台構圖全都在導演的腦海中,所以他總是坐在台下,以便完整模擬出觀眾的視覺效果,然後再不斷修改調整。對羅伯.威爾森導演來說,演員也是舞台的一部分,與布景道具環環相扣,必須整體考量。這樣的思考真的很令人佩服,也讓我受教了。
有一次排戲,導演坐在台下看,突然拿起麥克風問:「Ms. 唐,妳可以跳舞嗎?」我是個戲曲演員,跟跳舞完全沾不上邊,一時之間真的想不到可以跳什麼舞?只好跟導演說:「我想到什麼就跳什麼,沒有特定設計編排,可以嗎?」導演說:「Ok,隨興就好。」於是開始放音樂,當時我的扮相是卓別林,靈機一動就用卓別林的招牌舞步、帽子、拐杖跳舞。跳完他走上舞台,我心想一定沒過關,沒想到他竟然說很好,就這樣跳。我驚訝的說:「可是我剛才真的是隨興跳,根本不記得跳了什麼舞步。」導演回答:「不用擔心,妳剛才跳的舞步我都請副導記錄下來了。」這樣細膩的工作態度,又一次讓我折服。
又有一次排練,導演突然開口說:「Ms. 唐,妳可以唱出爵士樂的另外一種風格嗎?」我問:「哪一種?」導演說:「美國盲人歌手那種。」我問導演:「那是怎麼樣的唱法?」只見導演直接上台,跟道具人員拿了付墨鏡戴上,手上再拿根手杖,放起音樂示範給我看。我看了後只要求再多聽幾遍音樂,然後也戴上眼鏡開始唱,再一次接球成功。
還有一個角色是「飆車少年」,原本的設定是我一邊騎腳踏車一邊講話,可是到了舞台上怎麼騎都不順手,於是跟導演反映:「這樣會影響我的演出。」導演想了想,靈感忽然來了,問我有沒有看過穿皮衣戴墨鏡騎摩托車的「飆車少年」,我說看過。導演就要我演出急速騎車,然後停下來猛踩油門,用音效結合口技發出摩托車的吼聲。我這下真的傻眼了,演了一輩子戲還真沒用過這種技法,但還是硬著頭皮努力嘗試,沒想到也成功達成任務。旁邊人都笑著問:「唐老師,為什麼不管導演做出什麼要求,妳都可以達成啊?」
當然導演也不是一味丟球,他會先試演員接球的能力,可以順利接住甚至能有反饋,他才會再投第二個、第三個⋯⋯並不是一次性的丟出許多角色,我才能一再挑戰自己的能力與極限。在這些過程中,我自己其實玩得很開心,從一個角色變出那麼多不同的角色,真讓我過足了戲癮,也發現表演真是全方位的展現。
羅伯.威爾森導演做事非常細膩,工作時完全投入而且相當嚴格,一收工卻像個大孩子般,是個幽默又Nice的人,我和導演雖然語言不通,只能用很簡單的破英文加上比手畫腳溝通,但我們對工作的熱忱和不設限的工作態度,以及對表演藝術求完美的想法是一致的,這應該就是合作愉快最大的主因吧!
首次接受西方文化撞擊,功力大增
從前我作為演員是依照導演給的功課練習,但這次合作完全不依劇本行事,導演每天都在推翻原來的劇本,這是一般演員很少面臨的考驗與學習。這時我就非常感謝自己的成長背景,小時候長期獨處練就我冷靜不易驚慌的個性,演出外台戲更要隨時應變突發狀況,隨著環境迅速適應。這些舊有經驗讓我不畏懼的迎接挑戰,也才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在工作態度上,我從導演身上學到堅持、對工作負責,也對想做的事情永不放棄,真的好奇妙,導演的這些工作態度正是媽媽平日告誡我做人處事的精神。導演的開放態度也讓我深刻體會到,作品的創作在一開始雖然是自己的,但一旦推上舞台就是屬於所有人的,可受公評與借鏡。因而創作必須有突破的勇氣,才能為未來留下值得參考的演出經驗。
合作過程中,我得以近距離觀察導演帶來的合作班底,示範西方劇場的工作型態,也看到導演的創造與構思方式。導演的視覺美學也有自己的一套方式,這對我日後在歌仔戲舞台創作上有很大的激發。過去是打亮取光,現在則學會以舞台、影像、演員、燈光為整體考量,讓整個舞台更具整體性。
回想和導演的合作一轉眼已近十年,這是我首次受到西方文化的撞擊,幸好沒被撞昏還讓我功力大增,感謝這個機緣,讓這些學習成為我豐富劇團的珍貴養分。
(本文未完,全文請見圓神出版社《人生的身段:堅毅慈心唐美雲》
【更多內容請上圓神出版。書是活的粉絲專頁,或圓神書活網;本文由圓神出版提供,未經授權,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