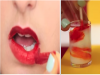學了那麼多戀愛的技巧,懂了那麼多所謂的人情世故,在一個傍晚推開酒館的門,卻聽過路的旅人說,女孩已經登船走了。
你把該想的都想好,舞台上的山水雲霧,明月大江,身上穿的長袖冠帽,金刀鐵馬,都準備得穩妥,簾子一開,就等一個人落淚。
我知道很多人像你,很努力的準備,開幕奏樂,結果位子空著,鼓聲越來越急,迴蕩在不大不小的劇場裡,銅鑼一響,你發現,人沒來。
其實感情有時候,就是挺無奈的。
我以為曲聲一響,就有夢幻,我以為俯下身來,就有娟紅。
但可能我想得還是簡單了。
我最喜歡陳升的《牡丹亭》,有一次我一個人開車,電台裡主播說,讓我們播一首老歌,男主播說,是什麼歌呢,女主播說,你猜,男主播說,我猜不到,女主播說,她說了什麼我忘了,但是音樂出來,是陳升的這首歌,陳升的聲音就像台北的老男人,他心裡在說,猜你MB,我要開始抒情。
黃粱一夢二十年,依舊是,不懂愛也不懂情。
陳升這個人一抒情,就是大浪淘沙,弄得人沉默,劉若英也是這樣,這兩人的歌,聽著都挺無奈的,兩手一攤,我沒什麼辦法。
感情裡無奈的一面,就是你現在面對的情況,談不上為什麼,因為有時候找感情不是動一寸進一寸的問題,有人說談戀愛我當然要努力,火力全開,這個我不攔你,巋然不動確實沒有什麼勝算,但是我今天要說的是,火力全開,也未免能全盡其功。
我記得那天,這首歌的歌詞和我一起穿梭在高聳的樓宇之間,我也奇怪,為什麼我一直無法遇到一個,我喜歡的人,又或者我曾經喜歡的人,為什麼一個也沒有留住。
再過幾年,但凡你有過回憶的人,都要結婚了,但凡你信誓旦旦的人,你早就不在乎了,這時候,你輕而易舉的就可以累覺不愛,你走下舞台,很容易就成了一個通透的人,沒有牽掛與眷戀,成為了一個獻身於為人民服務事業的,大寫的人,正直,善良,風趣,五官端正。
但是你誰也不愛,你成了身邊人的燈塔,勸他們這樣,那樣,但你誰也不愛,誰也不愛你,我一想到這,就感到恐慌。
我覺得你某種程度,和我一樣恐慌,讓你全心全意的人,在哪,你不知道,多少年過去,你不可能再為了一個人騎二十公里,只為了說一句我到了你下樓,你不單不可能,你還要嗤之以鼻,你一定非常的恐慌。
儘管你小心翼翼的保留,但似乎一鬆手,就要雲散,你立馬就要化身成鐵人,無堅不摧。
可誰要這種無堅不摧。
方丈說,看破紅塵,方丈那麼牛逼,女人跟人跑了,看破了紅塵,幾十年過去,方丈在山下摘一朵桃花,卻發現根本記不起女人的樣子,佛祖說,成了,圓滿。
方丈淚流滿面。
小和尚問,師父,你是開心嗎,方丈搖搖頭。
你只要不想等,不願信,你站起來,關燈,收拾乾淨,拍屁股走人,出來你就是鐵人,沒有人傷得了你,但這應該不是你想要的。
我覺得我們苦苦追尋,苦苦搏命,最後在喝大酒的夜晚看見哥們和他的女人走了,留下你一個人影子被路燈拉得老長,我知道你會問自己一些,為什麼我要一個人,是不是我就要一個人。
你想起華英雄裡陳浩南說自己命犯了什麼天煞的孤星,一頭白髮,老婆死在大火裡。
你就容易變成那些自作堅強的鐵人,看破一些莫名其妙的紅塵。
這世上容易的,就是看破紅塵,難的,恰是命裡打滾,輕而易舉,說一些不痛不癢,都是沒想明白。
我倒是更願意勸慰自己,可能就是時候沒到,我雖然不知道這個時間要等多久,我也一個人面對舞台,感到束手無策,我那麼迫不及待的要一個女人,其實還是不懂感情。
我以為我跋山涉水,穿過了森林草地,就什麼都能搞定,但感情的答案似乎也不在這裡。
我準備得再好,並不能換來愛情。
後來我明白,感情不是我打十個怪,升五級,感情真的是刷一輩子,才爆出一把的武器。
有時候,愛情就是要等,與你的能力,財富,情商有關,可你有了它們,所向無匹,結果還是要等。
我不是來勸你成為一個什麼優秀的人,或者什麼放浪的情種,我是想告訴你,當你覺得自己已經有了一切,並不能代表,你就能擁有愛情。
耐心等,你一放棄,你就化身鐵人。
無堅不摧,看破紅塵。
這世上好多人等的不耐煩了,就說我這輩子不需要女人,不需要男人,我要一個人活,走遍世界,成為一個孤傲的旅人,他們就看破紅塵,隨處布道,可我不願意,我覺得,爛就爛在這,功德圓滿,我滿不了。
如果你覺得自己沒有問題,那麼就只能坐下來等,你一個人等。
時鐘在響,你很急,你想,放他媽的狗屁,根本就已經來不及。
我和你一樣,也在想,是不是這個人來過,我卻不小心把她攆了出去,還是她錯過了班機,根本沒有想到這裡。
你坐在台上問自己,搞這麼一出,有什麼意義呢,大風吹呀吹,誰有閒工夫看戲。
我所有的煙花只能一瞬,但是這一瞬,只有這一瞬,我不能錯過你。
我由衷的希望,在散場的最後一秒到來之前,空蕩蕩的劇場裡走進來一個人。
可能她沒有多好看,也沒有多聰明,她躡手躡腳的選了一個邊角的位子,傻乎乎地看著你,劇場的燈光不多不少,不明亮也不昏暗,它們恰到好處的勾勒在她或圓或尖的臉額上。
因為風寒而微微發紅的鼻頭,因為溫暖而微微飽滿的唇肉。
你就一定要說:
等你很久啦。